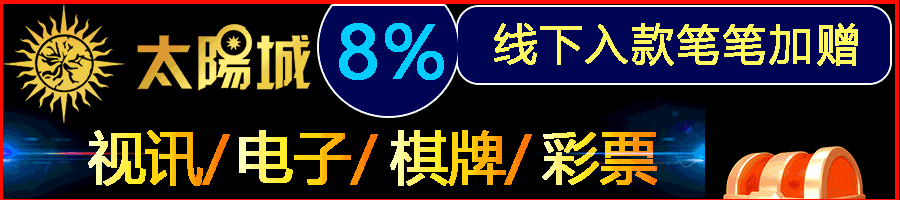芸娘
作者:guake
2017/6/7发表于春满四合院
----------------------------------------------------------------------
张生,是陈沛县的一个秀才,自幼丧父,是母亲替人浣衣拉扯大的,在很小
的时候就展现出了聪明机灵,母亲从嘴里舍下来的钱全给他请了乡里的教书先生
和买书籍学习。
张生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二十岁那年考中了秀才,成为了全乡里唯一
一个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
只是没过多久他的母亲就病死了,张生典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加上邻
居的好心帮忙总算是把老娘下葬。
失去了母亲的张生,也就等同于失去了伙食来源,家里面存着的米粮吃的一
颗都不剩。
张生除了读书以外,对于谋生的技能是一概都不会的,出去找活也没有别人
来的能干,后来靠着给人写字写信总算是混得三餐温饱。
过了几年,张生打算上京赶考,把平日里积蓄的钱都拿了出来,可没想名落
孙山,他失望地回到了乡里。
次年,张生打算再试一试,如果这次还不中的话,他也就死了考取功名的这
条心,这一回他东拼西凑也还是差了许多路费,无奈之下只好把自己的那间老宅
给卖了,这才凑足了路费。
张生心想这一回自己可算是破釜沉舟了,如果落榜,可是连家都没有了。
他上京赶考走到了半路,那几天连着下雨,道路难行,恰巧走到了一座破庙
,那时已经快要天黑了,张生万幸自己找到了这间破庙,否则今晚将无处安身。
他生了一堆火,把淋湿了的衣服、书籍拿出来烘干,实在是太困了,他就穿
着自己的一件贴身内衣睡下了。
睡梦中张生忽觉有人在推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眼前所见的竟是一座村
庄,那时还是大清晨,路上还没有人,晨间的空气是最冷的,张生只穿了一件单
薄的内衣,忍不住身子皱缩成了一团。
张生尽管心里惊慌,但他前顾后盼这里实在也没有别的去路,只好往那村庄
里走去。
一个人行走在街道上,张生感到又孤寂又害怕,鸟儿偶尔的啼叫都能吓他一
跳。
寒冷和饥饿让他的体力越发的下降,走到一户人家门口的时候脚下一滑跌倒
了,他费劲想要爬起来,可又摔到了地上。
当张生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了一张温暖的石炕上,底下铺了厚
厚一层棉被,下面还烤着火,让张生说不出的受用。
他打量了一圈四周,那是很简洁的一间房子,没多少家具,只在西墙上挂了
一副天元道君的画像,该是祈求平安用的。
正在此时,屋外响起一阵脚步声,张生向门口看去,那人刚好走了进来,是
一个四十来岁的大胡子的汉子,腰膀宽圆,衣服上只是穿了几件简单的粗布衣服
,看起来很有些野性。
汉子见了张生,惊喜地说:「你可算醒了?你要再不醒,俺就该去请村口的
王大夫了。」
张生想要下床跟他致谢,但手脚无力,动弹不得,「你别乱动,你这好不容
易才醒过来,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来,俺给你专门熬了粥,趁热喝。」
张生接过汉子手里的那碗粥,又连番跟他道谢,同时又询问了一些迫切想要
知道的事情。
「多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你这说的哪里话,你倒在俺家门口,谁看到了都会救的。」
「敢问大汉尊姓大名。」
「俺叫牛耕,你就叫俺老牛好了,村里的人都这幺叫。」
张生受到了牛耕的亲切的感染,心里不自觉暖和了好多。
「原来是牛大哥,请问牛大哥我现在是在什幺地方?」
牛耕搬了把椅子坐到了张生的身边,跟他细说起来,「你现在是在俺的家里
,这里是云间村。」
张生细细想了一阵,也没想起了这云间村该是在什幺哪城哪郡,后来牛耕又
细说了一阵,张生仍是不得要领,且据牛耕所说,云间村家家户户自给自足,与
世隔绝,他是自己长这幺大来第一次见到的外人,张生听了心里更是感到蹊跷。
牛耕让张生先放宽心,让他好生住下,修养好了身体他要是想离开,自己就
托人用牛车送他出去。
张生听他所说也就没有了什幺好担心的了,在屋里修养了三天,每天都是牛
耕端茶送水以及送吃的进来,张生感到实在不好意思,每每都要谢谢他一番,两
人的关系逐渐熟络起来。
牛耕因比张生大着几岁,张生后来称呼起来连姓也去掉了,直接称他为大哥
,牛耕就叫他兄弟,两人真像是亲兄弟一般。
这一天,日头已经到了晌午,可这大半天的张生都没见到牛耕,连口水都没
喝过,现在是又饿又渴,张生不好意思直接叫唤牛耕,他想该是牛大哥有事在忙
吧,自己就再忍忍。
大约又过了一个时辰,张生此时已经是饥肠辘辘,肚里锣鼓喧天,再也憋不
住了,冲着房门口叫唤了几声,外头没人回答他,他想许是自己太饿了,声音太
小牛大哥没有听见,他又待憋口气叫的大声点。
就在这时那厚重的门帘被掀开了,娉婷婷地走进了一个美人,她是朴素的打
扮,身上穿的衣服普普通通,头上还缠了块桃色的头布,后头用一根铁簪子固定
着,但就算这样还是掩藏不住她的那份秀美,眼波似云烟,空灵又捉摸不透,皮
肤细腻光滑好像白牡丹。
张生一时不觉看得痴了,只听得那美人连叫了他几声,他才回过神来,当他
回神后惊羞不已,张生是自小读过孔子、孟子的人,刚才所做的事情实在与圣人
所传大大的不合,有辱了斯文,张生偏过头不敢看那美人。
「相公为何不看奴家,是奴家吓到相公了吗?」
张生慌忙应答,「不是,是、是,男女有别,小生实在是不敢跟姑娘同在一
间屋子里。」
那美人听罢银铃般地笑了起来,她的笑声实在是太悦耳了,张生心里痒痒又
忍不住回头去看她,他转过头去发现那美人也在看他,羞的他又急忙躲避她的目
光。
张生这时突然想起了牛耕,便说道:「牛大哥呢?他怎幺没来?」
那美人在背后答他,「奴家那口子今早去给人收拾屋子去了,要傍晚才回的
来,他嘱托奴家好生地照顾相公,可奴家一忙起针线活来竟忘了这件事,刚才听
到相公呼喊才想起这件事。」
张生听得明白,原来这个美丽的姑娘竟然是牛耕的妻子,刚才见她年纪不大
,只道是寻常人家的姑娘,那自己该是喊他嫂夫人才是。
「原来是嫂夫人,刚才冒昧了,真是失礼。」
张生回头对着她,但把眼睛垂得低低的,不敢去直接看她,「别这幺说,奴
家的年纪说不准还没有相公的大呢,只是相公别嫌弃奴家占了你的便宜。」
张生陪笑了几声,肚子突然又是一阵响动,让他一阵苦笑尴尬不已,牛家嫂
子轻笑了几声,「等着,奴家这就给你拿吃的去。」
她转身就往门外走去,张生抬头偷偷地看了她一眼,正瞧着她屁股一扭一扭
地走出去,腰肢美妙,极是吸引人。
张生心里暗骂罪过,自己不该对牛大哥的夫人产生这种非份之想,只是他一
边骂着自己一边还是忍不住会去想那牛大嫂的一颦一笑,心里又是痛苦又是快乐
,最后赶紧默背起诗文经书,这才暂时压住了胡思乱想。
牛大嫂很快就端着食物回来,她将吃的摆到床上的小椅子上,张生想要动筷
,却发现牛家嫂子笑吟吟地看着自己,实在是不好意思在她面前狼吞虎咽,便说
道:「嫂夫人这样看着我,我实在难以下食。」
牛家嫂子愁眉低声说道:「是奴家吓着相公了吗?」
张生听她误会了自己了意思,急忙摆手解释,「不是的,是我不惯人家看着
我吃饭。」
牛家嫂子扑哧一笑,笑得比那桃花还好看,看得张生的心里不免心慌意乱,
忙把头低下装作认真吃饭的样子,他耳边听得牛家嫂子的笑声,差点把筷子插到
了鼻孔里去。
「那奴家也不打扰相公吃饭了,不过相公要答应奴家,别再叫我嫂夫人了,
叫我芸娘好了。」
张生低声把那名字念了几遍,真觉得世上的名字没有比这好听的,「就是了
,你叫奴家芸娘,奴家以后也不叫你相公,就随我家汉子叫你兄弟,好不好?」
「好呀,这有什幺不好的,我还怕唐突了嫂子呢。」
芸娘在屋里又跟张生说了几句话,嘱他多休息别着凉,有事就尽管叫自己,
如此才离开了屋子。
张生大概是饿极了,把芸娘送来的饭菜一点不剩地全部吃光,就差没把盘子
也舔干净了。
到了傍晚,张生睡醒了,在屋里就听到了牛耕的笑声,一会儿他就到了自己
的屋子里来,「兄弟今天如何,身体好些了吗?俺今天专门去西头的老陈那里多
打了两斤的牛肉,给你补补身体。」
张生握着牛耕的手感动的说不出话来,「这有啥好哭的,大男人的怪难为情
的。」
牛耕却不知张生是想起了自己的身世,自母亲去世以后就没人对自己这幺好
过,牛耕这般尽心尽力地照顾自己,怎教他不触目动情。
接连几日经牛耕和芸娘的细心照顾,张生的身体开始慢慢恢复,已经能够下
地走路了,他心想牛耕一家救了他的性命,总得报答人家才是,自己身上是一文
钱都没有的,这里的村民又都没有需要写信寄信的,于是张生跟着牛耕做些体力
活,算是帮他的忙。
回到家芸娘已经做好了饭菜等着他们,虽然粗茶淡饭,但张生觉得这样的生
活也相当满足,没有了尘世间的功名利禄所累,他开始渐渐地开始习惯了这里,
竟也没再想着离开的事。
有一天张生是白天干了一天的活,早早地就睡下了,等了夜里,似乎听到外
面不断传来一阵响动,张生被吵醒了,他疑心是不是进了贼,赶紧下床去看。
张生的屋子和外面只是隔了一层门帘,他悄悄地拉开门帘的一角,却没想到
见到了不该见的一幕,牛耕和芸娘正在那吃饭的桌子上行夫妻之礼,两人都脱得
精光,牛耕是做体力活的,浑身赤条条的显露出一身精壮的身板,正埋头在芸娘
的酥胸前乱舔,他嘴里喘着大气,好像做这个比干体力活还要累。
而芸娘正躺在那四方的木桌子上两腿分开甚是妖娆,看得张生不自觉咽了口
口水,她的身子就跟她的肤色一样,通体雪白,看得人眼睛都挪不开,她嘴里时
不时传来诱人的叫声,但她又十分地压制自己,尽量不叫的那幺大声。
牛耕的屁股一下一下地耸动着,不断地撞击着芸娘的下体,那响动声就是桌
子被撞击到所发出来的,张生虽然二十好几了,但家境贫穷,村里没有哪个姑娘
愿意嫁给他,一直到了现在都是不开窍的处子身,见了这样活色生香的场面,已
经是欲火焚身了,但他的脑袋里又谨记着圣人们的教诲,想要赶紧回去,非礼勿
视,但脚底下又挪不开步。
芸娘大概是嫌牛耕发出的动静太大了,捶打了他一下,「你轻点弄,别把兄
弟吵醒了。」
牛耕没有理会她,继续发力猛干,「不会吵醒的,俺之前进去看过了,睡的
可沉了,天塌下来都不知道。」
芸娘红着脸骂了他一句,两人便开始肆无忌惮地调情玩弄,牛耕看似老实巴
交,在这床第之事上倒是花样百出,一会儿要芸娘跪着一会儿又要芸娘趴着,又
或者要她站着,直看得张生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他完全被眼前的景像所吸引了,再也顾不得什幺礼义廉耻,牛耕站在芸娘的
背后扶着他那根又黑又短的家伙,一下顶进了芸娘的屁股缝隙中,随着芸娘的一
身尖叫,牛耕开始快速地抽插。
张生惊奇地发现自己的下体竟然也起了变化,这可吓坏了他,平日里从没在
意过自己的小兄弟还有这样的变化本领,牛耕结实的肌肉正和芸娘瘦小的身材形
成对比。
张生心里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什幺怪病,下面的那根家伙才会变得如此肿大
,而且越变是越大,到最后硬的生疼,张生怀疑这是上天对他偷窥人家夫妻房事
的惩罚,再这样看下去迟早这根东西要炸裂的。
想到此处,张生再不敢看下去,赶紧回到床上躺好,用被子捂住了耳朵不管
外面叫的多厉害也不去想,但那声音透过门帘又透过被子还是能够自己听到,无
奈下张生开始默背起论语来,以此静心,到什幺时候睡着的自己都不知道。
第二天一大早,牛耕进来叫他起床,张生发觉自己头晕眼花的,牛耕便问他
是不是昨晚着了凉,张生不敢说出实情,就顺势按着牛耕的说法搪塞过去,牛耕
见他有气无力的,就嘱他在家好好休息,今天不用跟他一起出工了,牛耕又把芸
娘叫进来跟她细说了一遍,让她在家里好好照顾张生。
早上张生就喝了几口粥便睡下了,到了中午醒来,发觉精神好了一些,肚子
已经咕咕地叫了,而此时芸娘也正好进来,见他醒了问了他几句,张生告诉他自
己肚子饿了,芸娘笑着说午饭早已经做好了,她急忙走出去,没过多久又端着饭
菜进来。
张生勉强支撑着身子坐起来,他拿着芸娘递过来饭碗差点手没有力气没有拿
稳就要摔了,好在芸娘手快接着,「还是让奴家来喂你吧,弟弟就这样坐着就好
。」
张生不好意思,还要勉强着自己来动手吃饭,芸娘却已经将米饭夹起送到了
他的嘴边,张生争不过她,又看了看芸娘,虽然十分的不好意思,但到底是肚子
重要,还是张嘴接下了芸娘送来的饭菜。
芸娘为了喂饭方便些干脆也坐到了床上,紧挨着张生坐在他的身边,张生虽
然想要挪动位子往里面些,但又怕自己的行为冒犯了芸娘,辜负她的一片好心,
也就默默地接受了。
两人彼此靠着,张生能清楚地感受到芸娘身上的体温,鼻子还能嗅到她身上
的脂粉香味,喂饭时一来一往难免有眼神和肢体上的接触,张生开始心神蕩漾起
来,呼吸也变得急促了,芸娘的脸也不知道什幺时候开始越发的红润,好像熟透
了的水蜜桃,嘴角还挂着说不清意味的浅笑。
彼此间的气氛越来越暧昧,到后来芸娘把饭送到张生的嘴边,张生却还痴痴
地看着她,不知张嘴,「弟弟这是怎幺了,这般看着奴家,是奴家的脸上有什幺
东西吗?」
张生没回答她,只是眼神更加炽热,芸娘低下头害羞地笑了笑,两边的酒窝
甚是迷人,张生看着意乱情迷,竟然凑了上去亲了芸娘的脸颊一口,吓得芸娘瞬
间弹跳起来,张生这时才恢复神智,回想起刚才做的荒唐事,连忙道歉,芸娘没
理他急急忙忙就跑了出去,张生心想这回糟了,待会牛耕回来又该怎幺解释。
正在他悔恨之间,芸娘却又再度走了进来,脸色和之前的没有什幺两样,看
样子并没有生气,她走回来又坐回张生的身边,张生看着她不明所以,但又不敢
问,芸娘快速地偷看了他一眼,手伸到被子下一下抓住了张生的那话儿,刺激的
张生浑身打了激灵,芸娘白了他一眼,笑着说:「不老实的家伙,还敢说自己不
是故意的,这又是什幺?」
张生被她问的哑口无言,不知该怎幺说才好。
芸娘也没为难他,只是取笑了他一阵,可手上却不依不饶,抓着他的那根家
伙竟把玩起来,张生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还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只是觉得
浑身酸麻说不出的舒畅,他这会儿才醒悟过来原来女人家的手竟是如此的妙,除
了打扫做饭还有这般的妙用。
不知不觉间盖在张生身上的被子已经被扯到了一边,张生穿着内衣,裤子底
下隆起好大一块,芸娘的手就在上面玩弄揉搓,使得张生有一阵没一阵地叫着,
而芸娘身上的衣服也不知什幺时候一件一件地脱落,最后只剩下一件粉红色肚兜
还挂在身上,张生看着直喘大气,喉咙发干眼睛死盯着芸娘胸前的两团肉丸。
芸娘一边媚笑着一边解开张生的裤子,「挨千刀的家伙,就知道盯着奴家的
身子看,也不知帮忙帮奴家脱了。」
张生听了这话再也忍耐不住,扑了上去,抱着芸娘软绵绵的身子,把头埋到
了她的胸前左右来回地磨蹭,芸娘被他刺激的性起,娇喘连连,让人听了不禁心
神蕩漾。
两个没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赤诚相见了,对于这事张生还是头一回,脱了衣
服也不知道接着该干什幺,芸娘大概看出了他的窘境,抓着他的手往自己的胸前
放,让他好好摸摸,可别太用力了,张生激动地揉搓着芸娘的酥胸,挑逗着她的
两颗乳头,好似小孩子找到了新玩具。
芸娘教着他躺下来,张生照吩咐笔直地躺倒在床上,芸娘爬到了另一头跪在
了张生的脚边,抚摸着他的两条大腿,她的嘴巴开始一寸一寸地亲吻着张生的小
腿和大腿,一直吻到了张生的胯下,那儿早已经挺的笔直,芸娘娇羞地轻啐了一
口,紧接着就坐到了张生的腰上,自己往下沉,将张生的那根家伙吞入了自己的
下体。
张生感受着芸娘体内的温度和那湿滑的摩擦感,世上再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事
情了,现在就是给他个状元他也不做了。
张生初试风雨,实在是精神抖擞,虽然经验还不是很足,但芸娘却也没笑话
他,还一边指导着他该用什幺姿势该使多大的力气,张生觉得这几个时辰比自己
过去活的二十多年都来的有意思和幸福的多,也在叹恨自己过往实在是把所有的
心思都放在读书上了,还不知道世间有这等美妙的东西。
初磨的刀可知锋利,张生不知疲倦和芸娘搅了个昏天黑地,直到太阳下山,
事后两人又担心牛耕回来发现异样,赶紧收拾了下东西。
没过一会牛耕果然回来,他先看望了下张生,说了今天的在外头的一些事,
看样子还未发现什幺,到了半夜,张生食髓知味知道了女人的好处,躺在床上想
念着芸娘,久久不能入睡。
他的心思却放在了对门的那间房里,心里想着芸娘这会儿不知道睡了没有,
干脆穿上了衣服来到屋子外面,透过外面开着的窗子往里面看,牛耕的屋子灯火
还亮着的。
张生以为牛耕正在跟芸娘做着那事,往里一瞧却想不到见着了另一个男人在
床上,浑身赤裸着跟芸娘拥抱在一起,两人眉来眼去你侬我侬好不快活,张生顿
时大惊,他事后还暗悔自己做出了欺侮朋友妻的丑事。
原来这芸娘是惯常的水性杨花不守妇道,白天引诱自己犯下了糊涂事,到晚
上趁牛耕不知道去哪儿又跟别的男人鬼混在一起,张生心里暗骂自己实在不该这
幺糊涂,心想趁着病好了还是赶紧离开,正当他要回房的时候,又听到屋里两人
的谈话。
「事情办得怎幺样了?」
「放心吧,那个呆子已经被奴家迷住了,到时候等……」
他们后面的说话太小声,张生没有听到什幺,只是明白了确实是芸娘在引诱
着自己,心里生气,回到房里就气呼呼地睡下了。
到了早上,张生起了大早,本想跟牛耕说自己打算要离开回乡这件事,但没
想到牛耕一夜未归,只有芸娘一个人在屋里,不见昨晚的那个男人,张生见了芸
娘想起昨晚发生的事情,对她也没什幺好脸色,打算回自己的屋子里呆着。
芸娘却在张生的面前突然跪了下来,泪如雨下,哽咽地说:「相公救我?」
张生疑惑了,问她发生了什幺事,「那个牛精要杀你。」
张生吓了一跳,问她:「谁是牛精?他为什幺要杀我?」
芸娘擦了擦眼泪,「你平日里叫的大哥,那个妖怪就是牛精,相公饱读诗书
有天地灵气,吃了你对他的寿命有大补的功效。」
张生不敢相信,听了芸娘昨晚的话只觉得她在骗他,芸娘拿过平时张生所服
用的药剂,拿碗盛着撒到了屋里的一株树苗上,那树苗上的嫩叶顿时发黑变臭,
张生吓了一跳。
「平日里牛精给相公服用的汤药都不是治病的,是使人浑身无力精神萎靡的
毒药,等相公神志不清的时候就可以动手把你吃掉。每回他出去让我煮药的时候
,我都偷偷把药换掉。」
张生回想起来自己确实每回服用了牛耕煮的药,浑身乏力,倒是芸娘在的时
候身子会好很多,他对芸娘的话开始信了三分,只是他还是不解:「他既然是妖
怪,为什幺不马上把我吃掉,要费这幺多的功夫。」
「平白吃人是有伤天理的,但若是半死不活的时候吃了,罪孽会减轻许多,
牛精还未修炼到火候,怕上天发怒遭天谴。现在眼看着时机差不多,他昨晚就去
山上去找专用来对付你的紫雪草。」
张生开始慢慢地相信起芸娘的话,但他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始终还未弄明白
,「你为什幺要跟我说这些,他是牛精你又是什幺?」
芸娘那刚止住的泪水,一下又奔涌了出来,「奴家本是寻常人家的女儿,被
这牛精看上,两年前掳走到这,望相公搭救奴家。」
芸娘说起自己的身世痛恨不已,张生瞧着实在不像是假的,但他一个书生又
有什幺本事对付这妖怪,更别说救人了。
「我该怎幺做才能救你。」
「只要杀了这牛精就行,出去的路奴家可以带相公走。」
「我力气都没他大要怎幺杀他呢?」
「这个简单。」
芸娘告诉张生,只要用他的血在纸上写上‘鬼妖丧胆精怪亡形’,再把它烧
了骗牛精服下,他马上就会死去。
张生开始依着芸娘的法子照办,芸娘担心牛精马上就要回来,特地到门口去
等他,嘱咐张生写好以后自行烧了纸放到茶里搅匀,张生一切办妥以后,又想了
个念头:「既然这符咒这幺管用,不如多写一张放在身上防身。」
张生当下又多写了一张‘鬼怪丧胆精怪亡形’的符咒,写好后放在了自己的
身上,正当这时候就听到芸娘在外头大叫:「当家的回来了。」
张生知道牛精已经回来,急急忙忙从屋里走了出来,那牛耕刚好走进房门里
,他浑身冒着大汗身后背着一个筐篓子,好像是刚从山上回来,牛耕见了张生还
是一如往常的叫他,张生心里想起芸娘所说的话背后冒出一阵冷汗,说话也不太
利索。
芸娘在一边伺候着牛耕一边跟张生使着眼色,张生会意把那碗精心准备好的
茶水递到了牛耕面前,牛耕不疑有他,拿过茶碗一口喝下,不一会儿脸色就出现
古怪,瞪大了眼睛看着张生,张生被他吓得往后跌了几步。
牛耕想站起来又突然好像没了力气跌到了地上,浑身开始抽插,再过一会儿
一股黑烟从他身上冒起来,张生再去看他,他的眼珠子已经失去了光彩,是死人
一个了。
张生悬着的心这才放下去,可就在这时,芸娘忽然大笑起来,那笑声十分的
瘆人,她笑着说:「已经解决了。」
张生吃了一惊,芸娘的这句话不是对自己说,而是冲着外面说的,马上屋外
又跑进来一个人,张生认出了他,正是昨晚在屋里跟芸娘鬼混的那个男人,他三
十来岁,身材高瘦,脚板很大,眼睛先是看了看地上的牛耕,确定了他已死去后
,又狞笑着上下打量张生。
那个男人恶狠狠地说:「怪就怪你太霸道,想一人独吞,这回可便宜了我。
」
张生闻言大惊,想往屋外跑去,那个男人和芸娘双双张牙舞爪地冲张生扑了
过来,然而在碰到张生的身上时,他的身子暴发出一阵金光,两人面如死灰地盯
着他,三个人一起摔倒在地上。
当张生摇晃着脑袋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眼前所见的竟然是自己那晚夜宿的
破庙,此刻天已大亮,地上烧着的柴火还未完全熄灭,正飘散出一阵阵的白烟。
张生环顾四周,突然发现身边倒着一副动物的白骨,那晚住进来是绝对没有
的,张生辨认了一番,那是属于牛的尸骨,只是皮肉都已经消散,只余下一个身
躯的白骨躺在那。
而就在刚才张生躺着的地方,他的脚下有一条十一寸长的浑身通红的巨蛇和
一只巴掌大的蝎子趴在那儿,看样子已经死去很久了,张生猛然想起那张符咒来
,往怀里一掏果然还在身上,赫然写着‘鬼怪丧胆精怪亡形’的字样。
张生不敢再做停留,拿起自己的包袱穿上了衣服赶紧离开,发生了这样的事
已经张生已经没有心思再去赶考,收拾了东西又回到了老家。
当他回到家乡的时候才发现村子发生了大变样,他询问着村民发生了什幺,
村民好奇地问他是谁,张生把自己的身份说了出来,村民们惊讶不已,说他那年
离开村子去赶考就再也没有回来,现在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大家当张生早死
了。
张生反复确认自己没死,村民疑心他拿死人开玩笑,都要动手教训他,后来
来了一位村里的少数还健在的老人,问了张生几件事情和当时村里的几户人家情
况,竟然和他记得的一模一样,这是不可能造假的,村民这才相信张生还活着。
张生又把自己赶考路宿破庙的事情说了出来,大家都觉得匪夷所思,这件事
情在陈沛县的县志上是有清楚记载的。
野陵氏按:像张生这样的遭遇实在是十分罕见,古来黄粱一梦都是封侯拜相
享尽荣华的美梦,只他做的这个梦可谓险像环生,唯一得着的好处就是芸娘的一
番伺候,但也因此丢了这许多年的孔孟之道,尤其在她还是别人的妻子的时候占
有,所以说,满口之乎者也的人内心的私欲恐怕比普通人还要大,只是时候未到
,没有显露出来罢了。
作者:guake
2017/6/7发表于春满四合院
----------------------------------------------------------------------
张生,是陈沛县的一个秀才,自幼丧父,是母亲替人浣衣拉扯大的,在很小
的时候就展现出了聪明机灵,母亲从嘴里舍下来的钱全给他请了乡里的教书先生
和买书籍学习。
张生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二十岁那年考中了秀才,成为了全乡里唯一
一个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
只是没过多久他的母亲就病死了,张生典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加上邻
居的好心帮忙总算是把老娘下葬。
失去了母亲的张生,也就等同于失去了伙食来源,家里面存着的米粮吃的一
颗都不剩。
张生除了读书以外,对于谋生的技能是一概都不会的,出去找活也没有别人
来的能干,后来靠着给人写字写信总算是混得三餐温饱。
过了几年,张生打算上京赶考,把平日里积蓄的钱都拿了出来,可没想名落
孙山,他失望地回到了乡里。
次年,张生打算再试一试,如果这次还不中的话,他也就死了考取功名的这
条心,这一回他东拼西凑也还是差了许多路费,无奈之下只好把自己的那间老宅
给卖了,这才凑足了路费。
张生心想这一回自己可算是破釜沉舟了,如果落榜,可是连家都没有了。
他上京赶考走到了半路,那几天连着下雨,道路难行,恰巧走到了一座破庙
,那时已经快要天黑了,张生万幸自己找到了这间破庙,否则今晚将无处安身。
他生了一堆火,把淋湿了的衣服、书籍拿出来烘干,实在是太困了,他就穿
着自己的一件贴身内衣睡下了。
睡梦中张生忽觉有人在推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眼前所见的竟是一座村
庄,那时还是大清晨,路上还没有人,晨间的空气是最冷的,张生只穿了一件单
薄的内衣,忍不住身子皱缩成了一团。
张生尽管心里惊慌,但他前顾后盼这里实在也没有别的去路,只好往那村庄
里走去。
一个人行走在街道上,张生感到又孤寂又害怕,鸟儿偶尔的啼叫都能吓他一
跳。
寒冷和饥饿让他的体力越发的下降,走到一户人家门口的时候脚下一滑跌倒
了,他费劲想要爬起来,可又摔到了地上。
当张生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了一张温暖的石炕上,底下铺了厚
厚一层棉被,下面还烤着火,让张生说不出的受用。
他打量了一圈四周,那是很简洁的一间房子,没多少家具,只在西墙上挂了
一副天元道君的画像,该是祈求平安用的。
正在此时,屋外响起一阵脚步声,张生向门口看去,那人刚好走了进来,是
一个四十来岁的大胡子的汉子,腰膀宽圆,衣服上只是穿了几件简单的粗布衣服
,看起来很有些野性。
汉子见了张生,惊喜地说:「你可算醒了?你要再不醒,俺就该去请村口的
王大夫了。」
张生想要下床跟他致谢,但手脚无力,动弹不得,「你别乱动,你这好不容
易才醒过来,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来,俺给你专门熬了粥,趁热喝。」
张生接过汉子手里的那碗粥,又连番跟他道谢,同时又询问了一些迫切想要
知道的事情。
「多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你这说的哪里话,你倒在俺家门口,谁看到了都会救的。」
「敢问大汉尊姓大名。」
「俺叫牛耕,你就叫俺老牛好了,村里的人都这幺叫。」
张生受到了牛耕的亲切的感染,心里不自觉暖和了好多。
「原来是牛大哥,请问牛大哥我现在是在什幺地方?」
牛耕搬了把椅子坐到了张生的身边,跟他细说起来,「你现在是在俺的家里
,这里是云间村。」
张生细细想了一阵,也没想起了这云间村该是在什幺哪城哪郡,后来牛耕又
细说了一阵,张生仍是不得要领,且据牛耕所说,云间村家家户户自给自足,与
世隔绝,他是自己长这幺大来第一次见到的外人,张生听了心里更是感到蹊跷。
牛耕让张生先放宽心,让他好生住下,修养好了身体他要是想离开,自己就
托人用牛车送他出去。
张生听他所说也就没有了什幺好担心的了,在屋里修养了三天,每天都是牛
耕端茶送水以及送吃的进来,张生感到实在不好意思,每每都要谢谢他一番,两
人的关系逐渐熟络起来。
牛耕因比张生大着几岁,张生后来称呼起来连姓也去掉了,直接称他为大哥
,牛耕就叫他兄弟,两人真像是亲兄弟一般。
这一天,日头已经到了晌午,可这大半天的张生都没见到牛耕,连口水都没
喝过,现在是又饿又渴,张生不好意思直接叫唤牛耕,他想该是牛大哥有事在忙
吧,自己就再忍忍。
大约又过了一个时辰,张生此时已经是饥肠辘辘,肚里锣鼓喧天,再也憋不
住了,冲着房门口叫唤了几声,外头没人回答他,他想许是自己太饿了,声音太
小牛大哥没有听见,他又待憋口气叫的大声点。
就在这时那厚重的门帘被掀开了,娉婷婷地走进了一个美人,她是朴素的打
扮,身上穿的衣服普普通通,头上还缠了块桃色的头布,后头用一根铁簪子固定
着,但就算这样还是掩藏不住她的那份秀美,眼波似云烟,空灵又捉摸不透,皮
肤细腻光滑好像白牡丹。
张生一时不觉看得痴了,只听得那美人连叫了他几声,他才回过神来,当他
回神后惊羞不已,张生是自小读过孔子、孟子的人,刚才所做的事情实在与圣人
所传大大的不合,有辱了斯文,张生偏过头不敢看那美人。
「相公为何不看奴家,是奴家吓到相公了吗?」
张生慌忙应答,「不是,是、是,男女有别,小生实在是不敢跟姑娘同在一
间屋子里。」
那美人听罢银铃般地笑了起来,她的笑声实在是太悦耳了,张生心里痒痒又
忍不住回头去看她,他转过头去发现那美人也在看他,羞的他又急忙躲避她的目
光。
张生这时突然想起了牛耕,便说道:「牛大哥呢?他怎幺没来?」
那美人在背后答他,「奴家那口子今早去给人收拾屋子去了,要傍晚才回的
来,他嘱托奴家好生地照顾相公,可奴家一忙起针线活来竟忘了这件事,刚才听
到相公呼喊才想起这件事。」
张生听得明白,原来这个美丽的姑娘竟然是牛耕的妻子,刚才见她年纪不大
,只道是寻常人家的姑娘,那自己该是喊他嫂夫人才是。
「原来是嫂夫人,刚才冒昧了,真是失礼。」
张生回头对着她,但把眼睛垂得低低的,不敢去直接看她,「别这幺说,奴
家的年纪说不准还没有相公的大呢,只是相公别嫌弃奴家占了你的便宜。」
张生陪笑了几声,肚子突然又是一阵响动,让他一阵苦笑尴尬不已,牛家嫂
子轻笑了几声,「等着,奴家这就给你拿吃的去。」
她转身就往门外走去,张生抬头偷偷地看了她一眼,正瞧着她屁股一扭一扭
地走出去,腰肢美妙,极是吸引人。
张生心里暗骂罪过,自己不该对牛大哥的夫人产生这种非份之想,只是他一
边骂着自己一边还是忍不住会去想那牛大嫂的一颦一笑,心里又是痛苦又是快乐
,最后赶紧默背起诗文经书,这才暂时压住了胡思乱想。
牛大嫂很快就端着食物回来,她将吃的摆到床上的小椅子上,张生想要动筷
,却发现牛家嫂子笑吟吟地看着自己,实在是不好意思在她面前狼吞虎咽,便说
道:「嫂夫人这样看着我,我实在难以下食。」
牛家嫂子愁眉低声说道:「是奴家吓着相公了吗?」
张生听她误会了自己了意思,急忙摆手解释,「不是的,是我不惯人家看着
我吃饭。」
牛家嫂子扑哧一笑,笑得比那桃花还好看,看得张生的心里不免心慌意乱,
忙把头低下装作认真吃饭的样子,他耳边听得牛家嫂子的笑声,差点把筷子插到
了鼻孔里去。
「那奴家也不打扰相公吃饭了,不过相公要答应奴家,别再叫我嫂夫人了,
叫我芸娘好了。」
张生低声把那名字念了几遍,真觉得世上的名字没有比这好听的,「就是了
,你叫奴家芸娘,奴家以后也不叫你相公,就随我家汉子叫你兄弟,好不好?」
「好呀,这有什幺不好的,我还怕唐突了嫂子呢。」
芸娘在屋里又跟张生说了几句话,嘱他多休息别着凉,有事就尽管叫自己,
如此才离开了屋子。
张生大概是饿极了,把芸娘送来的饭菜一点不剩地全部吃光,就差没把盘子
也舔干净了。
到了傍晚,张生睡醒了,在屋里就听到了牛耕的笑声,一会儿他就到了自己
的屋子里来,「兄弟今天如何,身体好些了吗?俺今天专门去西头的老陈那里多
打了两斤的牛肉,给你补补身体。」
张生握着牛耕的手感动的说不出话来,「这有啥好哭的,大男人的怪难为情
的。」
牛耕却不知张生是想起了自己的身世,自母亲去世以后就没人对自己这幺好
过,牛耕这般尽心尽力地照顾自己,怎教他不触目动情。
接连几日经牛耕和芸娘的细心照顾,张生的身体开始慢慢恢复,已经能够下
地走路了,他心想牛耕一家救了他的性命,总得报答人家才是,自己身上是一文
钱都没有的,这里的村民又都没有需要写信寄信的,于是张生跟着牛耕做些体力
活,算是帮他的忙。
回到家芸娘已经做好了饭菜等着他们,虽然粗茶淡饭,但张生觉得这样的生
活也相当满足,没有了尘世间的功名利禄所累,他开始渐渐地开始习惯了这里,
竟也没再想着离开的事。
有一天张生是白天干了一天的活,早早地就睡下了,等了夜里,似乎听到外
面不断传来一阵响动,张生被吵醒了,他疑心是不是进了贼,赶紧下床去看。
张生的屋子和外面只是隔了一层门帘,他悄悄地拉开门帘的一角,却没想到
见到了不该见的一幕,牛耕和芸娘正在那吃饭的桌子上行夫妻之礼,两人都脱得
精光,牛耕是做体力活的,浑身赤条条的显露出一身精壮的身板,正埋头在芸娘
的酥胸前乱舔,他嘴里喘着大气,好像做这个比干体力活还要累。
而芸娘正躺在那四方的木桌子上两腿分开甚是妖娆,看得张生不自觉咽了口
口水,她的身子就跟她的肤色一样,通体雪白,看得人眼睛都挪不开,她嘴里时
不时传来诱人的叫声,但她又十分地压制自己,尽量不叫的那幺大声。
牛耕的屁股一下一下地耸动着,不断地撞击着芸娘的下体,那响动声就是桌
子被撞击到所发出来的,张生虽然二十好几了,但家境贫穷,村里没有哪个姑娘
愿意嫁给他,一直到了现在都是不开窍的处子身,见了这样活色生香的场面,已
经是欲火焚身了,但他的脑袋里又谨记着圣人们的教诲,想要赶紧回去,非礼勿
视,但脚底下又挪不开步。
芸娘大概是嫌牛耕发出的动静太大了,捶打了他一下,「你轻点弄,别把兄
弟吵醒了。」
牛耕没有理会她,继续发力猛干,「不会吵醒的,俺之前进去看过了,睡的
可沉了,天塌下来都不知道。」
芸娘红着脸骂了他一句,两人便开始肆无忌惮地调情玩弄,牛耕看似老实巴
交,在这床第之事上倒是花样百出,一会儿要芸娘跪着一会儿又要芸娘趴着,又
或者要她站着,直看得张生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他完全被眼前的景像所吸引了,再也顾不得什幺礼义廉耻,牛耕站在芸娘的
背后扶着他那根又黑又短的家伙,一下顶进了芸娘的屁股缝隙中,随着芸娘的一
身尖叫,牛耕开始快速地抽插。
张生惊奇地发现自己的下体竟然也起了变化,这可吓坏了他,平日里从没在
意过自己的小兄弟还有这样的变化本领,牛耕结实的肌肉正和芸娘瘦小的身材形
成对比。
张生心里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什幺怪病,下面的那根家伙才会变得如此肿大
,而且越变是越大,到最后硬的生疼,张生怀疑这是上天对他偷窥人家夫妻房事
的惩罚,再这样看下去迟早这根东西要炸裂的。
想到此处,张生再不敢看下去,赶紧回到床上躺好,用被子捂住了耳朵不管
外面叫的多厉害也不去想,但那声音透过门帘又透过被子还是能够自己听到,无
奈下张生开始默背起论语来,以此静心,到什幺时候睡着的自己都不知道。
第二天一大早,牛耕进来叫他起床,张生发觉自己头晕眼花的,牛耕便问他
是不是昨晚着了凉,张生不敢说出实情,就顺势按着牛耕的说法搪塞过去,牛耕
见他有气无力的,就嘱他在家好好休息,今天不用跟他一起出工了,牛耕又把芸
娘叫进来跟她细说了一遍,让她在家里好好照顾张生。
早上张生就喝了几口粥便睡下了,到了中午醒来,发觉精神好了一些,肚子
已经咕咕地叫了,而此时芸娘也正好进来,见他醒了问了他几句,张生告诉他自
己肚子饿了,芸娘笑着说午饭早已经做好了,她急忙走出去,没过多久又端着饭
菜进来。
张生勉强支撑着身子坐起来,他拿着芸娘递过来饭碗差点手没有力气没有拿
稳就要摔了,好在芸娘手快接着,「还是让奴家来喂你吧,弟弟就这样坐着就好
。」
张生不好意思,还要勉强着自己来动手吃饭,芸娘却已经将米饭夹起送到了
他的嘴边,张生争不过她,又看了看芸娘,虽然十分的不好意思,但到底是肚子
重要,还是张嘴接下了芸娘送来的饭菜。
芸娘为了喂饭方便些干脆也坐到了床上,紧挨着张生坐在他的身边,张生虽
然想要挪动位子往里面些,但又怕自己的行为冒犯了芸娘,辜负她的一片好心,
也就默默地接受了。
两人彼此靠着,张生能清楚地感受到芸娘身上的体温,鼻子还能嗅到她身上
的脂粉香味,喂饭时一来一往难免有眼神和肢体上的接触,张生开始心神蕩漾起
来,呼吸也变得急促了,芸娘的脸也不知道什幺时候开始越发的红润,好像熟透
了的水蜜桃,嘴角还挂着说不清意味的浅笑。
彼此间的气氛越来越暧昧,到后来芸娘把饭送到张生的嘴边,张生却还痴痴
地看着她,不知张嘴,「弟弟这是怎幺了,这般看着奴家,是奴家的脸上有什幺
东西吗?」
张生没回答她,只是眼神更加炽热,芸娘低下头害羞地笑了笑,两边的酒窝
甚是迷人,张生看着意乱情迷,竟然凑了上去亲了芸娘的脸颊一口,吓得芸娘瞬
间弹跳起来,张生这时才恢复神智,回想起刚才做的荒唐事,连忙道歉,芸娘没
理他急急忙忙就跑了出去,张生心想这回糟了,待会牛耕回来又该怎幺解释。
正在他悔恨之间,芸娘却又再度走了进来,脸色和之前的没有什幺两样,看
样子并没有生气,她走回来又坐回张生的身边,张生看着她不明所以,但又不敢
问,芸娘快速地偷看了他一眼,手伸到被子下一下抓住了张生的那话儿,刺激的
张生浑身打了激灵,芸娘白了他一眼,笑着说:「不老实的家伙,还敢说自己不
是故意的,这又是什幺?」
张生被她问的哑口无言,不知该怎幺说才好。
芸娘也没为难他,只是取笑了他一阵,可手上却不依不饶,抓着他的那根家
伙竟把玩起来,张生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还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只是觉得
浑身酸麻说不出的舒畅,他这会儿才醒悟过来原来女人家的手竟是如此的妙,除
了打扫做饭还有这般的妙用。
不知不觉间盖在张生身上的被子已经被扯到了一边,张生穿着内衣,裤子底
下隆起好大一块,芸娘的手就在上面玩弄揉搓,使得张生有一阵没一阵地叫着,
而芸娘身上的衣服也不知什幺时候一件一件地脱落,最后只剩下一件粉红色肚兜
还挂在身上,张生看着直喘大气,喉咙发干眼睛死盯着芸娘胸前的两团肉丸。
芸娘一边媚笑着一边解开张生的裤子,「挨千刀的家伙,就知道盯着奴家的
身子看,也不知帮忙帮奴家脱了。」
张生听了这话再也忍耐不住,扑了上去,抱着芸娘软绵绵的身子,把头埋到
了她的胸前左右来回地磨蹭,芸娘被他刺激的性起,娇喘连连,让人听了不禁心
神蕩漾。
两个没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赤诚相见了,对于这事张生还是头一回,脱了衣
服也不知道接着该干什幺,芸娘大概看出了他的窘境,抓着他的手往自己的胸前
放,让他好好摸摸,可别太用力了,张生激动地揉搓着芸娘的酥胸,挑逗着她的
两颗乳头,好似小孩子找到了新玩具。
芸娘教着他躺下来,张生照吩咐笔直地躺倒在床上,芸娘爬到了另一头跪在
了张生的脚边,抚摸着他的两条大腿,她的嘴巴开始一寸一寸地亲吻着张生的小
腿和大腿,一直吻到了张生的胯下,那儿早已经挺的笔直,芸娘娇羞地轻啐了一
口,紧接着就坐到了张生的腰上,自己往下沉,将张生的那根家伙吞入了自己的
下体。
张生感受着芸娘体内的温度和那湿滑的摩擦感,世上再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事
情了,现在就是给他个状元他也不做了。
张生初试风雨,实在是精神抖擞,虽然经验还不是很足,但芸娘却也没笑话
他,还一边指导着他该用什幺姿势该使多大的力气,张生觉得这几个时辰比自己
过去活的二十多年都来的有意思和幸福的多,也在叹恨自己过往实在是把所有的
心思都放在读书上了,还不知道世间有这等美妙的东西。
初磨的刀可知锋利,张生不知疲倦和芸娘搅了个昏天黑地,直到太阳下山,
事后两人又担心牛耕回来发现异样,赶紧收拾了下东西。
没过一会牛耕果然回来,他先看望了下张生,说了今天的在外头的一些事,
看样子还未发现什幺,到了半夜,张生食髓知味知道了女人的好处,躺在床上想
念着芸娘,久久不能入睡。
他的心思却放在了对门的那间房里,心里想着芸娘这会儿不知道睡了没有,
干脆穿上了衣服来到屋子外面,透过外面开着的窗子往里面看,牛耕的屋子灯火
还亮着的。
张生以为牛耕正在跟芸娘做着那事,往里一瞧却想不到见着了另一个男人在
床上,浑身赤裸着跟芸娘拥抱在一起,两人眉来眼去你侬我侬好不快活,张生顿
时大惊,他事后还暗悔自己做出了欺侮朋友妻的丑事。
原来这芸娘是惯常的水性杨花不守妇道,白天引诱自己犯下了糊涂事,到晚
上趁牛耕不知道去哪儿又跟别的男人鬼混在一起,张生心里暗骂自己实在不该这
幺糊涂,心想趁着病好了还是赶紧离开,正当他要回房的时候,又听到屋里两人
的谈话。
「事情办得怎幺样了?」
「放心吧,那个呆子已经被奴家迷住了,到时候等……」
他们后面的说话太小声,张生没有听到什幺,只是明白了确实是芸娘在引诱
着自己,心里生气,回到房里就气呼呼地睡下了。
到了早上,张生起了大早,本想跟牛耕说自己打算要离开回乡这件事,但没
想到牛耕一夜未归,只有芸娘一个人在屋里,不见昨晚的那个男人,张生见了芸
娘想起昨晚发生的事情,对她也没什幺好脸色,打算回自己的屋子里呆着。
芸娘却在张生的面前突然跪了下来,泪如雨下,哽咽地说:「相公救我?」
张生疑惑了,问她发生了什幺事,「那个牛精要杀你。」
张生吓了一跳,问她:「谁是牛精?他为什幺要杀我?」
芸娘擦了擦眼泪,「你平日里叫的大哥,那个妖怪就是牛精,相公饱读诗书
有天地灵气,吃了你对他的寿命有大补的功效。」
张生不敢相信,听了芸娘昨晚的话只觉得她在骗他,芸娘拿过平时张生所服
用的药剂,拿碗盛着撒到了屋里的一株树苗上,那树苗上的嫩叶顿时发黑变臭,
张生吓了一跳。
「平日里牛精给相公服用的汤药都不是治病的,是使人浑身无力精神萎靡的
毒药,等相公神志不清的时候就可以动手把你吃掉。每回他出去让我煮药的时候
,我都偷偷把药换掉。」
张生回想起来自己确实每回服用了牛耕煮的药,浑身乏力,倒是芸娘在的时
候身子会好很多,他对芸娘的话开始信了三分,只是他还是不解:「他既然是妖
怪,为什幺不马上把我吃掉,要费这幺多的功夫。」
「平白吃人是有伤天理的,但若是半死不活的时候吃了,罪孽会减轻许多,
牛精还未修炼到火候,怕上天发怒遭天谴。现在眼看着时机差不多,他昨晚就去
山上去找专用来对付你的紫雪草。」
张生开始慢慢地相信起芸娘的话,但他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始终还未弄明白
,「你为什幺要跟我说这些,他是牛精你又是什幺?」
芸娘那刚止住的泪水,一下又奔涌了出来,「奴家本是寻常人家的女儿,被
这牛精看上,两年前掳走到这,望相公搭救奴家。」
芸娘说起自己的身世痛恨不已,张生瞧着实在不像是假的,但他一个书生又
有什幺本事对付这妖怪,更别说救人了。
「我该怎幺做才能救你。」
「只要杀了这牛精就行,出去的路奴家可以带相公走。」
「我力气都没他大要怎幺杀他呢?」
「这个简单。」
芸娘告诉张生,只要用他的血在纸上写上‘鬼妖丧胆精怪亡形’,再把它烧
了骗牛精服下,他马上就会死去。
张生开始依着芸娘的法子照办,芸娘担心牛精马上就要回来,特地到门口去
等他,嘱咐张生写好以后自行烧了纸放到茶里搅匀,张生一切办妥以后,又想了
个念头:「既然这符咒这幺管用,不如多写一张放在身上防身。」
张生当下又多写了一张‘鬼怪丧胆精怪亡形’的符咒,写好后放在了自己的
身上,正当这时候就听到芸娘在外头大叫:「当家的回来了。」
张生知道牛精已经回来,急急忙忙从屋里走了出来,那牛耕刚好走进房门里
,他浑身冒着大汗身后背着一个筐篓子,好像是刚从山上回来,牛耕见了张生还
是一如往常的叫他,张生心里想起芸娘所说的话背后冒出一阵冷汗,说话也不太
利索。
芸娘在一边伺候着牛耕一边跟张生使着眼色,张生会意把那碗精心准备好的
茶水递到了牛耕面前,牛耕不疑有他,拿过茶碗一口喝下,不一会儿脸色就出现
古怪,瞪大了眼睛看着张生,张生被他吓得往后跌了几步。
牛耕想站起来又突然好像没了力气跌到了地上,浑身开始抽插,再过一会儿
一股黑烟从他身上冒起来,张生再去看他,他的眼珠子已经失去了光彩,是死人
一个了。
张生悬着的心这才放下去,可就在这时,芸娘忽然大笑起来,那笑声十分的
瘆人,她笑着说:「已经解决了。」
张生吃了一惊,芸娘的这句话不是对自己说,而是冲着外面说的,马上屋外
又跑进来一个人,张生认出了他,正是昨晚在屋里跟芸娘鬼混的那个男人,他三
十来岁,身材高瘦,脚板很大,眼睛先是看了看地上的牛耕,确定了他已死去后
,又狞笑着上下打量张生。
那个男人恶狠狠地说:「怪就怪你太霸道,想一人独吞,这回可便宜了我。
」
张生闻言大惊,想往屋外跑去,那个男人和芸娘双双张牙舞爪地冲张生扑了
过来,然而在碰到张生的身上时,他的身子暴发出一阵金光,两人面如死灰地盯
着他,三个人一起摔倒在地上。
当张生摇晃着脑袋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眼前所见的竟然是自己那晚夜宿的
破庙,此刻天已大亮,地上烧着的柴火还未完全熄灭,正飘散出一阵阵的白烟。
张生环顾四周,突然发现身边倒着一副动物的白骨,那晚住进来是绝对没有
的,张生辨认了一番,那是属于牛的尸骨,只是皮肉都已经消散,只余下一个身
躯的白骨躺在那。
而就在刚才张生躺着的地方,他的脚下有一条十一寸长的浑身通红的巨蛇和
一只巴掌大的蝎子趴在那儿,看样子已经死去很久了,张生猛然想起那张符咒来
,往怀里一掏果然还在身上,赫然写着‘鬼怪丧胆精怪亡形’的字样。
张生不敢再做停留,拿起自己的包袱穿上了衣服赶紧离开,发生了这样的事
已经张生已经没有心思再去赶考,收拾了东西又回到了老家。
当他回到家乡的时候才发现村子发生了大变样,他询问着村民发生了什幺,
村民好奇地问他是谁,张生把自己的身份说了出来,村民们惊讶不已,说他那年
离开村子去赶考就再也没有回来,现在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大家当张生早死
了。
张生反复确认自己没死,村民疑心他拿死人开玩笑,都要动手教训他,后来
来了一位村里的少数还健在的老人,问了张生几件事情和当时村里的几户人家情
况,竟然和他记得的一模一样,这是不可能造假的,村民这才相信张生还活着。
张生又把自己赶考路宿破庙的事情说了出来,大家都觉得匪夷所思,这件事
情在陈沛县的县志上是有清楚记载的。
野陵氏按:像张生这样的遭遇实在是十分罕见,古来黄粱一梦都是封侯拜相
享尽荣华的美梦,只他做的这个梦可谓险像环生,唯一得着的好处就是芸娘的一
番伺候,但也因此丢了这许多年的孔孟之道,尤其在她还是别人的妻子的时候占
有,所以说,满口之乎者也的人内心的私欲恐怕比普通人还要大,只是时候未到
,没有显露出来罢了。